放假
MissLee放假一個月,回饋祖國,八月中旬再會。
家長日說得最多的話︰
家長問︰「佢讀文科商科定理科好呢﹖」
MissLee︰「如果弟日唔係做醫生建築師工程師藥劑師,咁讀邊科都無所謂…但係佢數理唔得,理科就唔好諗啦。佢個人怕悶,讀商科就有趣d;中史同文學要背好多野,佢唔鐘意背,就要諗諗。但係佢個人唔識轉彎,會考歷史問題好值接,佢容易應付,我驚佢讀經濟會唔明喎。」
家長問︰「咁,即係讀咩適合佢呢﹖」
MissLee︰「讀書睇興趣啦,佢未大定既,只要唔係想做醫生,弟日升大學仲有好多出路既。」
家長皺晒眉。(即係點﹖)
MissLee︰「唔洗決定住,返屋企諗下先啦。」
學生同家長遲早會發現,成績表上的評語同家長會的說話只係左抄右抄。學生,來來去去都係果幾款。
免費的《頭條日報》創刊,李太話浪費紙張。我今天一人拿了兩份免費報紙,自己再買一份,家裡又有另一份。加上垃圾宣傳,李宅每天總棄掉不少紙張。
《頭條》屬星島系,今天的內容不斷宣傳兩個訊息,一是要辦一份「開心、正面」的報紙,另外強調「人人做記者」,報館會送上薄酬。
報紙的創刊詞頗為有趣。它指出「頭條新聞是重要新聞,報紙不同版面都有頭條,不但嚴肅新聞有頭條,娛樂新聞有頭條,即使風花雪月的八卦新聞皆有頭條」。
如果略懂新聞和報館運作,為了照顧讀者閱讀需要,突出重點是撰寫和排版的必然考慮因素。如果這也是《頭條》的賣點,則只能做到編採的基本要求,即沒有賣點!
創刊詞又指「人生充滿壓力,社會也充斥不幸的消息,死人塌樓的突發聞無日無之,《頭條日報》雖然也會報道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意外消息,但我們我希望多報道令人愉快的新聞,讓大家抱持樂觀積極的心情,開展新一天的工作」,所以《頭條日報》的辦報宗旨是「開心、樂觀、積極」。
作為創刊詞,這段詞的中文水平不但與MissLee一樣,水皮又欠文采,我尤其怕那種「樂觀開心」的定義。我想其所指的樂觀不單是乾乾淨淨沒有死人塌樓,而是不作批評建制的政治乾淨。看今天的頭條,「嫡系中資入股亞視」,新聞爆炸力與平民吸引力欠奉,明顯是交心與交貨之作。所謂開心的報紙也不單指不報道煽腥色,而是真的以客觀平實、以知識論知識的態度報道。
 所以我喜歡看都巿日報。就算它好像Florence所說是「炒雜錦」,但它很努力地追求不偏不倚地「炒」消息,兼愈來愈厚,不乏有份量的作者和文章,加上與雜誌及電視台聯系刊登資訊與趣味性強的文章,如每週的新潮電器介紹,偶爾刊登有線和無線新聞特輯的文字版,不買信報與不看書的早上,我都喜歡拿一份來看,由銅鑼灣看到調景嶺也未必看完;也樂意讓都巿日報入學校,讓學生取閱。
你可以話我有偏見。學校去年只為學生教師訂星島,我日日讀到血壓高。星島令我覺得它濫用新聞自由為集團旗下產品和老闆作個人宣傳,但手法拙劣,令人「血脈沸騰」也。
至於「全民做記者」兼爆料有錢派($100-5000),能否成事,會否鼓勵假新聞仍難下斷言。國內的報紙也會來這一套,我在首都最喜歡看的《新京報》便會以報酬吸引讀者爆料。隱約記得早前國內曾下令禁止賞賜讀者的新聞,出自何處則忘記了。見諒。
不過自由社會,商業運作,你有你做,我有我不看。
所以我喜歡看都巿日報。就算它好像Florence所說是「炒雜錦」,但它很努力地追求不偏不倚地「炒」消息,兼愈來愈厚,不乏有份量的作者和文章,加上與雜誌及電視台聯系刊登資訊與趣味性強的文章,如每週的新潮電器介紹,偶爾刊登有線和無線新聞特輯的文字版,不買信報與不看書的早上,我都喜歡拿一份來看,由銅鑼灣看到調景嶺也未必看完;也樂意讓都巿日報入學校,讓學生取閱。
你可以話我有偏見。學校去年只為學生教師訂星島,我日日讀到血壓高。星島令我覺得它濫用新聞自由為集團旗下產品和老闆作個人宣傳,但手法拙劣,令人「血脈沸騰」也。
至於「全民做記者」兼爆料有錢派($100-5000),能否成事,會否鼓勵假新聞仍難下斷言。國內的報紙也會來這一套,我在首都最喜歡看的《新京報》便會以報酬吸引讀者爆料。隱約記得早前國內曾下令禁止賞賜讀者的新聞,出自何處則忘記了。見諒。
不過自由社會,商業運作,你有你做,我有我不看。
又放暑假,是2004年度大事回顧的時候。
傳聞我是被特別指派任教這班,品行不好,成績也不好。一年下來,成績穩步上掦,但水平仍然偏低,與其他班距離很遠,相距約四分一「馬位」。臨放暑假前又出事,同事笑說班主任太「騎呢」,所以學生都「騎呢」。
我 跟他們數本年發生過的事,欺凌、上課秩序混亂、多人情緒失控、偷竊、破壞公物、拳打腳踢、校服不合規格、帶違禁品回校,平均兩星期一單。這個數字在某些學 校算平常了吧,皇仁都衰到上報紙。但處理每個個案都花時間心力,再加上炮製校本課程、帶課外活動、持續進修,自己都情緒失控。
所以前幾天班裡又有大件事,令我兩年來第一次想唔撈。「咩人黎嫁,教極都係咁,識唔識反省同自律嫁。」就係唔識囉,否則就不用教了。
教育實在是很大很大的課題。最近看Edward Said的Out of Place。Said小時候就不是能在學校獲取成功的人。特別是他在埃及唸英式和美式上流社會學校,規舉一板一眼,Said拿美國護照的阿拉伯裔身份,面孔、語言、名字與其他學生之不同,更加深了他在學校的格格不入。他的父母親極力改造他,從禮儀、性格與體能之培養、性知識的壓抑,令Said加倍反叛煩躁,也享受不到父親的愛。
全書共十一章,都在訴說他少年時的不安。讀到第九章,Said到美國升學,遇到老師Baldwin,才第一次解放了他的桎梏。教英語的Baldwin叫學生論如何燃點火柴,Said不斷翻閱科學書,有系統地以術語解答。Baldwin向學生反建議,何不觀察人是如何燃點火柴﹖是想放火把森林燒掉了,還是在洞穴點燃蠟燭﹖抑或打個比喻,是想照亮一個未明的世界﹖由此,Said發現他尋的不是客觀存在的領土,而是思想的領土。他第一次得到解放。少年一事無成的Said,後來成為卓越的學者。是學校太框限了這個人,是學校遺忘了這個人。
他 在書裡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指父母無不想創造子女。學校也在以規條創造學生,灌輸意識形態。要不要規條﹖怎樣的規條才不會妨礙學生發展﹖但學校不可無規。不 諱言,我們創校之初強調沒有校規缺點,一切靠學生自愛自律,但三年下來發現百病叢生,要把學生拉回正軌,所以規條愈來愈多,才能漸叫「正常」。
這也必須與教學成效與家長壓力拉在一起說。沒有一套明確的校規,單是自律令學生有恃無恐,犯事沒有後果,部份無法駕馭學生的教師管理課室失效,達不到客觀以成績品德為目標的傳統教學標準,家長教事齊齊煩躁。只有重回「常態」,教師才可以安心教書收工。
有些外國的學校,校規就只有一條,如尊重,如愛。我只要我的學生尊重別人,尊重自己,那上堂不會喧嘩,不會欠交功課,不會對其他同學作無禮行為,諸如此類。在本校經驗令我深信社化對管理社會的重要。
性本惡﹖所以才要教。性本善﹖所以學生才可以教。
摘自今天信報︰
劉健威引述今年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展館的問外語︰
Blame everyone, admits nothing. 埋怨所有人,什麼都不承認。
不過自己有時真係廢話。學生覺我廢話的時候更多。「Miss,今次我考試合唔合格﹖」答曰︰「應合格既合格,唔應合格既咪唔合格囉。」車~~
***
劉健威樓上呀梁燕城話,何志平藝術文化修養都幾好嫁,研究過孔孟老莊,驚訝於他的學問修養胸襟視野。何太胡慧中又係勁,連《左傳》都能答上兩咀。
修養同能力係無關係既,任得你文化修養幾好,管治架構不容許你發揮所長,加上屁股指揮腦袋,咁真係浪費晒d廣闊胸襟囉。何志平平日響明報副刊既短文又真係幾「平」,平平無奇、平舖直述。唔知我誤會了何志平為人呀定係深受我校部份老師景仰既梁燕城啦。
曾幾何時我都認為曾俊華幾好嫁,唔單止識建築藝術,仲去睇東宮西宮,仲唔係眼光遠大胸襟廣闊之人﹖佢前幾日話港台不應與商營電台重覆製作同類節目,應發展小眾節目,一道指令下來,人心惶惶,立即扣曾氏分,其為人尚待觀察。
***
噢,都係今日信報,六蚊,梗係用到盡。
毛孟靜分析,既然政府希望港台成為「小眾電台」,咁就更加要聘請黃毓民與鄭經翰齊齊開咪。曾蔭權競選,大班全力助選,親政權人物是也。商台與毓民中止合約,毓民不容於商辦電台,即無巿場效益也,佢阿哥仲唔係小眾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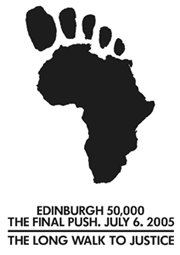 我似乎不應悲觀,但如Live 8音樂會的力量可以有多大﹖和古巨基楊千嬅容祖兒來唱反貪、清潔香港、擁護基法,又有什麼的不一樣﹖
我似乎不應悲觀,但如Live 8音樂會的力量可以有多大﹖和古巨基楊千嬅容祖兒來唱反貪、清潔香港、擁護基法,又有什麼的不一樣﹖
眾星透過Live 8宣傳「滅貧」(可以嗎﹖這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嗎﹖)的信息,我記得在新聞看到的是一輛巴士車身寫上 ‘make poverty history’,然後是U2、Bjork、東京、愛丁堡。
Live 8強 調跨國界、一條心,不要錢,一雙腿走出公義。但我所知現今的貧窮問題的成因包括不公平貿易、勞工剝削、國家貪污、缺乏民主甚至只是一套國家正常運行的制度 等。無論發達國家減少貧國幾多國債,如貧國欠缺適當運用貸款及捐款的制度,這些血汗錢終會付之流水,就如最近報章曾探討南亞海嘯的捐款,有六成捐款沒有兌 現。賑災、音樂會、什麼馬拉松籌款都只是富國的公關宣傳。
Live 8是一場資本主義糖衣包裝的賑災show。根據BBC的Live 8 blog報道,巨星坐著limo到場,在震耳欲聾的音響器材襯托下又唱又跳,互聯網將影像即時放到全世界,號稱有幾多個億的人正收看節目。
我真心相信U2的Bono真心關注貧窮問題,只是年青樂迷在音樂會華麗的包裝亢奮下,回到家,會冷靜反思自己的生活形態的人數真叫人擔心。就如早前Armstrong推出的Live Strong手帶,本意藉得推許,但當好意變成潮流口號,連麥記都有得換手帶,潮流便會消磨盡本意。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起點啊,或許某天某人記起曾參加過這樣的一場音樂會,夜靜時份,會心血來潮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呢,像我們的7.1。對,不過我覺得那些錢、贊助、巨星的叫喊可以用得更好罷了。我寧願政府花多點心思在教育身上,好過叫走音歌星們唱好香港。
G8今年關注點之一是非洲。那邊廂,在山間採集咖啡豆與飽受愛滋病的兒童婦女,不會知道那邊廂有人為一場「滅貧」的音樂會而瘋狂,甚至不知互聯網正轉播一場與他們有「深切關係」的音樂會,或者,沒有見過電腦。
我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在年尾香港那場世貿示威感到亢奮。
Live 8網頁︰ http://www.live8live.com/
***
我的自閉症又加深發作,啊,三天的假期啊~ 李太話,只見我不停行出行入攞隻碟響處食食食,暑假快點來吧,我要去旅行啊~
我忍唔住又響巴士聽人講野。今次係幾個坐響後排的男生。
「整咩餅好呢﹖」
「cheese cake囉,嗱,好簡單姐,響超級巿場買d消化餅,blend左佢,然後買卡夫d cream cheese,原味個隻,blend左佢,就得架啦。」
曉整餅的男生,份外吸引。「整咩西餐好呢…」抑或係學廚﹖
(轉話題)
「呢,間St. Mary d 女仔,英文都幾好喎。頭先果幾個應該係St. Mary既。」
噢,係應屆中五會考生。
「St. Mary響邊度﹖」…「近油尖旺。」
「好似港島都有一間喎。」…「響堅道,好似叫…咩St. Mercury…」
吓﹖美少女戰士Sailor Moon﹖Sorry, Miss Lee即刻攞左本筆記簿出黎,記低上述對話。
「St. Margaret呀吓﹖」…「都好似啱既…」
喂,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學校名都有得好似係﹖
咁,如果係會考生,Miss Lee的要求便會提高一點。唔係blend左d消化餅,應該係crush。唔係St. Mary,係St. Mary’s,d學生英文應該係幾好既。St. Mercury,真係無聽過。
***
忘不了個多月前壹仔訪問蘇絲黃的一篇文章。
「蘇施黃罵人無數。
每日下午三時,她踏進商業一台直播室,主持《友誼萬歲》。當中有個遊戲環節,參加的聽眾要用英文報上名來,發音準確,才可出線。
第一位聽眾說:『My lamp is……』蘇施黃沒讓他說完便糾正——『係name,唔係lamp。我係唔同燈對話嘅。』便cut了他線。
第二位聽眾一樣「唔生性」。「My name is『Air撚』(Alan)。」
「英文只有Alan,無『Air撚』。」又被cut線。
她不介意得罪「米飯班主」。《飲食男女》的讀者請她教煮餸—— 「Please to told me how to make肉碎steam水蛋。」
蘇施黃這樣回覆——「Darling!『to』後面一定是『present tense』!沒有『to told』的,更沒有『please to told』的。正確英文應為:『Please tell me how to make egg custard with minced pork』。」讀者問的烹飪問題,她沒有回答。」
終於有人在這個BLOG反對我啦,終於來了。我這個人又「反政府」又「煽動」,無理由下下留言都係支持既,遲早會有人來「踩場」。呵呵。來吧,不過我不會持續筆戰,因為學期尾根本無時間,講明到時唔好話我縮頭烏龜啊。明天放假,陪你玩玩。 「支持政府的人都是simple and naive」不是我原本的意思。我是指一般香港人對議題的探討都不夠深入,加上傳媒反智,報道一窩蜂,轉瞬即逝,著眼quotable quotes,這都是危險的「民主」。I mean Hong Kong people in general can be simple and naïve. 用「最大公約數」來形容社會狀況在近期真的很流行,這一定是偏頗的評語。 但哈巴馬斯的公共空間在資訊急速爆棚的現代是奢侈的,嚴肅討論沒落是不爭的事實,這不單是香港獨有的現像。我喜歡看別人的BLOG,因為在大眾傳媒看不到的嚴肅,在網上尋求得到,互聯網讓我們有更大空間長篇大論。也因為多參詳了別人的BLOG,我更有動力鞭策自己,培養耐性思考。我實在是一個浮躁的人,是年紀學習沈澱了。 香港的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不只是投票也不單是遊行。最原始的希臘式民主都要經過辯論,要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來作決定,這些我都教了學生。民主不是遊行喊喊口號請客吃飯,所以民主黨的李永達參加特首「選舉」都會被人指摘無法激起社會對本地政策發展更深層的討論,一早打定輸數更不是今時今日應有的態度。 兼容並包是民主社會的一大特色,香港人歧視同性戀者、窮人、新移民、南亞裔肥人、醜人、單親、豬扒、byebye肉,就不能說是成熟的民主社會。你能包容我嗎﹖ 無名氏君(砌磋都留個名呀,不打不相識嘛),我在「民調二」一文指出的是民調的危險。如果我是逢政府必反,就不必暗踩鍾庭耀的民意調查無聊。我的學生去年中一已學習了數字玩弄的玄機。「理性」社會需要客觀分析與深層討論,如果政府有意以民為本,中央政策組就不妨公開民調樣本,需知如何抽樣調查及設訂問題大大影響民調結果。中策組在要求下星期二才公佈調查方法,就不是恰當的做法,沒誤導之實也有誤導之嫌,先不要說設題是否符合客觀調查應有的性質。如認為我寫得唔清唔楚,請移玉步去Alex處細味Prime Minister的精句。 話時話,我click去中策組網頁的「最新消息」,則只顯示泛珠三角的報告,策略發展委員會則仍沿用2000年曾蔭權為財政司長時的稱號,奇哉怪也,曾蔭權引用4月份的調查則不見影踪,望高人指點。 愛之心責之切。不喜歡你就干脆睇住你死啦,仲得閒贈你兩句﹖這些辦公室小智慧,係香港人都識。請各位愛國愛港人士不要衝上腦。 (謝謝九州與小老師的留言,有負厚望。不要浪費時間向他們解釋了,尤如向基督徒傳佛教或vice versa一樣,嗱,打比喻咋,千其唔好無限上綱話我踩任何宗教呀。)
每當李太接到各類型電話促銷和民意調查,都將立刻放大嗓門叫我去接聽,我會再分類然後以不同的態度,包括細心聆聽、半途而廢、粗聲粗氣、敷衍了事和與對方鬥智鬥力去處理。選哪種態度就視乎心情了。
早幾年讀大學還滿有雄心時,我會十分認真地回答調查員的問題。但近年愈來愈「求其」,因為我真的不懂怎樣將一個議題濃縮成三數秒內要回答的答案,而調查員又沒有與我討論背後的想法與週邊原因,覺得好無聊。
好像上星期港大的民意調查中心問曾蔭權的民望,問及「你估計曾蔭權做特首會比董建華做得好D定差D﹖」特首才上任幾天,整個「競選」過程又只面對他喜歡面對的人,而「當奴」和「當特首」(其實都係當奴)的工作性質不盡相同,又怎輕易作比較呢﹖
調查員又問李永達及詹培忠角逐特首提名有沒有增加或者減少我對他們的好感或反感。將二人放在曾蔭權之後問,對我來說突顯了李詹勇敢出來競逐的「正義」,因而給予較高分收。
講開又講,有時學生的答案真係幾好笑,例如我問影響本科學習的因素是什麼,有人竟說「自己識唔識寫那課的字」,而平日堂上小睡最多的同學,竟給我寫了全級最詳盡的評語,看來我是把她忽略得緊要。也有同學叫我控制自己的情緒,噢,當然,也先請你們提升上課的表現啊…
 曾蔭權引中央政策組去年及今年的民意調查,指巿民首重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其次才關心民主政制發展,所以今後政府落實施政會以此次序為依歸。
曾蔭權引中央政策組去年及今年的民意調查,指巿民首重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其次才關心民主政制發展,所以今後政府落實施政會以此次序為依歸。
先不論兩次調查能否作比較,中央政策組訪問了什麼人,問題的設定如何,調查誤差如何。看看今年4月調查巿民最關注的25項建議,有些是要我舉例也舉不上的,例如「舊區重建」、「實行中央屠宰」、「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鼓勵生育」、甚至「在添馬艦舊址興建立法會大樓及政府總部」等。
這些例子難舉,與我贊成或反對這些建議無關。而是這25項建議內容的針對性,並非一個民意調查隨便問問巿民,便能得出如此議題。換句話說,政府心中已有一籮議題,才拿出來叫巿民排序而得出結果。
多項建議中的「實現雙普選」排名13(中間有4項議題獲同等排名),將調查的框架濃縮在「雙普選」裡。我們來個推論,如果另有「實現立法會全面直選」與「實現普選行政長官」兩個選擇,加上立法會選舉距已超過半年,但行政長官「競選」新鮮滾熱辣,搖擺不定、深受環境影響抉擇的香港巿民,又可能選出不一樣的結果了。
這25項 議題是怎樣得出來的呢﹖還有沒有其他巿民關心的議題﹖參與調查的巿民能否選擇「其他」項目﹖抑或政府在調查前有否邀請巿民參與制訂調查議題﹖希望政府能予 以公佈。事實上經濟發展必須仰賴開放多元、包容性強的社會,政制檢討必須與經濟措施同步上馬改革。我不希望曾特首以此議題判斷我較關心經濟而政制發展可以 押後,甚至以這次調查為施政依歸。
我 還在想是否參加今年的七一遊行。像「同志帶領遊行」的原因不是我的考慮因素,雖然我想為什麼一定是同志,而不是傷殘、工人、新移民等弱勢群體;為什麼不是 中產﹖第一次七一中產發出的聲音也不小。抑或我們根本不須要指明誰帶領﹖另外,我們要怎樣的七一定位﹖如上年有人提出般,讓其「嘉年華化」下去﹖我今次去 的目的是什麼﹖就算要發聲,我要發的是什麼聲音﹖我還沒有想得很好。我要想,因為一向就不太喜歡遊行叫喊,很迷失。有空再說,眼睏得交關。
(明報美術圖片)
 Initial D
Initial D  想自己頗喜歡感覺速度,無論是慢食還是颷車,都能幻想出一像氛圍來。只有過山車免問,畏高。
李太一直反對我學駕車,因為我無錢養,唯有靠朋友接載。記得大學時有同學在晚上載我們一干人在吐露港公路上颷,我們打開車頂在尖叫(少女是喜歡尖叫的呵~)。然後經驗坐在朋友電單車尾在公路上的快感。原來車已開得很快,他說映在倒後鏡的我一臉自在,一張「不知死」的臉。坐在車後,有點涼,頭盔像要向後飛走,但路燈熣燦,總希望他能繞遠一點的路。後來朋友賣了電單車,我也少了跟他吃飯了。
電影「頭文字D」在速度的感覺上略嫌慢了點,不過MTV與漫畫式剪接成功補飛,汽車飄移擺動加上車胎磨擦公路的「之之」聲製造快感,還有酷男搭夠,一句型英帥靚正,MissLee high足成晚。
電影裡第一代AE86已無法滿足藤原拓海對速度的追求。拓海說,看東西愈來愈慢,因為他自己感受的速度愈來愈快,現存條件無法與他的慾望結合。快感與慾滿無限,但客觀環境有限,如何突破自我是人生的艱難。速度會令我們喪失感知四周的能力、喪失了「景深」。拓海放棄夏樹後加入車隊,就是失落後追求速度的忘我的補賞吧。
Paul Virilio是唯一我知道有談及速度的學者,如有其他推薦,請各位不吝賜教。他指五光十色的媒介引領我們走向速度的無盡追求,媒介成為「眼球的摸擬」,眼球卻失去感應世界的功能。其實不只是速度,過份彩色的影像已叫人頭疼,自己不能再一星期啃一厚疊潮流雜誌。不只因為過了那年紀,也因為發現自己會在狂颷的潮流裡頭迷失。
當社會的極速之手愈伸愈遠,我們才更需要「慢」下來,細味觸摸身邊事物的輪廓,否則生活只是一束流逝的光影,是須藤京一最後的翻車。
註︰我沒有看過原裝漫畫。
想自己頗喜歡感覺速度,無論是慢食還是颷車,都能幻想出一像氛圍來。只有過山車免問,畏高。
李太一直反對我學駕車,因為我無錢養,唯有靠朋友接載。記得大學時有同學在晚上載我們一干人在吐露港公路上颷,我們打開車頂在尖叫(少女是喜歡尖叫的呵~)。然後經驗坐在朋友電單車尾在公路上的快感。原來車已開得很快,他說映在倒後鏡的我一臉自在,一張「不知死」的臉。坐在車後,有點涼,頭盔像要向後飛走,但路燈熣燦,總希望他能繞遠一點的路。後來朋友賣了電單車,我也少了跟他吃飯了。
電影「頭文字D」在速度的感覺上略嫌慢了點,不過MTV與漫畫式剪接成功補飛,汽車飄移擺動加上車胎磨擦公路的「之之」聲製造快感,還有酷男搭夠,一句型英帥靚正,MissLee high足成晚。
電影裡第一代AE86已無法滿足藤原拓海對速度的追求。拓海說,看東西愈來愈慢,因為他自己感受的速度愈來愈快,現存條件無法與他的慾望結合。快感與慾滿無限,但客觀環境有限,如何突破自我是人生的艱難。速度會令我們喪失感知四周的能力、喪失了「景深」。拓海放棄夏樹後加入車隊,就是失落後追求速度的忘我的補賞吧。
Paul Virilio是唯一我知道有談及速度的學者,如有其他推薦,請各位不吝賜教。他指五光十色的媒介引領我們走向速度的無盡追求,媒介成為「眼球的摸擬」,眼球卻失去感應世界的功能。其實不只是速度,過份彩色的影像已叫人頭疼,自己不能再一星期啃一厚疊潮流雜誌。不只因為過了那年紀,也因為發現自己會在狂颷的潮流裡頭迷失。
當社會的極速之手愈伸愈遠,我們才更需要「慢」下來,細味觸摸身邊事物的輪廓,否則生活只是一束流逝的光影,是須藤京一最後的翻車。
註︰我沒有看過原裝漫畫。
 這個長髮美女在電話中稱呼自己Sarah。如不是她把美麗動人的頭髮向後一撥擱在我的報紙上,又怎會留意到美女的存在呢。
我這世女只留過豬尾辮,頭髮到肩膊就不耐煩得要把它立刻削掉,萬種風情的撥髮動作是這世也做不來的了。我甚至想自己有沒有做過正常「少女」(這個詞語總叫我雞皮疙瘩)都會做的東西呢﹖我的少女聯想是花、粉紅色、公仔,與尖叫。打開衣櫃,有時自己都喊悶,顏色真素啊,近年因為面青青,才多買了鮮色的衣服。
尖叫是最近發現的,因為學校的少女都愛尖叫。我的解釋是少女喜歡引人注意,表現自己青春無敵勁可愛。對,尖叫是唯一我在「少女」時代曾做過的事,甚至現在我都會尖叫,不,應該是時常慘叫,特別是打翻東西和「將自己撞埋牆」的時候。我是真的會行行下路突然失去平衡撞自己埋牆的。
***
放學時終於見到一點陽光。到Starbucks買了冰飲與自己慶祝,心裡叫一聲finally。
這個長髮美女在電話中稱呼自己Sarah。如不是她把美麗動人的頭髮向後一撥擱在我的報紙上,又怎會留意到美女的存在呢。
我這世女只留過豬尾辮,頭髮到肩膊就不耐煩得要把它立刻削掉,萬種風情的撥髮動作是這世也做不來的了。我甚至想自己有沒有做過正常「少女」(這個詞語總叫我雞皮疙瘩)都會做的東西呢﹖我的少女聯想是花、粉紅色、公仔,與尖叫。打開衣櫃,有時自己都喊悶,顏色真素啊,近年因為面青青,才多買了鮮色的衣服。
尖叫是最近發現的,因為學校的少女都愛尖叫。我的解釋是少女喜歡引人注意,表現自己青春無敵勁可愛。對,尖叫是唯一我在「少女」時代曾做過的事,甚至現在我都會尖叫,不,應該是時常慘叫,特別是打翻東西和「將自己撞埋牆」的時候。我是真的會行行下路突然失去平衡撞自己埋牆的。
***
放學時終於見到一點陽光。到Starbucks買了冰飲與自己慶祝,心裡叫一聲finally。
 Distanace and tears.
Distanace and tears.  我是個眼淺的人。這幾年,感動的淚卻流得少了。曾幾何時我以眼淚證自己的存在證明一些關係,現在連辯駁也放棄了。
這年頭,看著感動的小說電影,明明心裡是揪著的痛,痛了幾天,也搾不出幾滴眼淚。反而工作得累了,坐在浴室裡,它卻沒有預告地流;或者學生一疊報紙飛摘過來,不其然也會流。但這不是感動的淚。
那晚闊別15年的嬸母又再去國,把我揪緊,「捨不得你啊」,她說。水點就在眼裡轉了。我在計程車裡回味那句說話,腦裡重演那個擁抱。片言,但15年竟那麼長,對現代人真有點不可思議。那年3歲的堂弟今年都進大學了。距離沒有讓他的神態與我的弟弟有任何分別。我只能說太奇妙了,沒有其他形容詞。
這幾年我人變得冷漠。與他人的關係,我選擇,並抗拒結識新知,嫌煩。他日,我應該是個孤獨老人。
發嘮叨,完。
我是個眼淺的人。這幾年,感動的淚卻流得少了。曾幾何時我以眼淚證自己的存在證明一些關係,現在連辯駁也放棄了。
這年頭,看著感動的小說電影,明明心裡是揪著的痛,痛了幾天,也搾不出幾滴眼淚。反而工作得累了,坐在浴室裡,它卻沒有預告地流;或者學生一疊報紙飛摘過來,不其然也會流。但這不是感動的淚。
那晚闊別15年的嬸母又再去國,把我揪緊,「捨不得你啊」,她說。水點就在眼裡轉了。我在計程車裡回味那句說話,腦裡重演那個擁抱。片言,但15年竟那麼長,對現代人真有點不可思議。那年3歲的堂弟今年都進大學了。距離沒有讓他的神態與我的弟弟有任何分別。我只能說太奇妙了,沒有其他形容詞。
這幾年我人變得冷漠。與他人的關係,我選擇,並抗拒結識新知,嫌煩。他日,我應該是個孤獨老人。
發嘮叨,完。
李家30度炎熱天拜山。我那對ABC堂兄妹對中國人傳統的拜山方法反應各異。3歲時曾來港的哥哥觀察力不錯,守墓的石獅子、衣紙的款式,他都拿出來問,拜得非常認真。初次到亞洲的妹妹,非常抗拒煙霧彌漫,十足十小時候的我般臭脾氣。我們愛惜她,讓她留在廟裡,不用上山。換著以前的我﹖兜巴星捉左上山啦。
家裡年過50的男丁積極除去墓碑附近的雜草、寫衣包、砌燒豬,當然包括熱烈地吃蓋滿灰燼的燒豬。對自己,我只想到detached一字,冷眼旁觀叔伯兄弟動手動腳。不想徒手撕油淋淋的燒豬,也不想除雜草傷手。懶惰的我只適合到天主教墳場放下鮮花。
記 得小時候燒衣包吐一句「好唔環保」俾人鬧,到現在我也常懷疑一年才吃那幾炷香究竟够不够飽,一千幾百萬的冥鏹在通貨膨脹的地府够不够花。但擔心自己懷疑得 多,到自己百年歸老後無人給我燒這燒那,但原來真的要「食」香飽的時候,掛著十字架我還是誠心地上香,心裡希望耶穌有怪莫怪。
再想到上星期學校辦福音音樂會,五個人彈彈結他唱唱rock版聖詩,負責同事就高高興興地表示有6個學生因此表示信主,查實問卷是叫學生填在音樂會後會否對基督教有興趣。心想歸依一個宗教那有這麼簡單,平生最怕過份熱情的基督徒。
主啊主,我相信聖靈的存在,但祈求所有的相信都基於認真的考慮而非氣氛營造興奮的結果,阿門。
 RAINY NITE
在巴士上收聽十分鐘電台直播曾蔭權記者會,那是我聽個最湍急的記者會,但與回家後在電視上看見的,竟然有這麼一點點分別。
傍晚六時四十分扭開收音機,大概七、八個記者發問問題吧,不停環繞行政會議的組成、他會否在兩年任期後角逐新任特首等問題,只聽見新的特首不停打斷記者的發問,以強而有力斬釘截鐵的語調回答,「沒有」、「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對記者關注針對的問題,他了然於胸,但斷然拒絕友善溝通的感覺很強。記者每條發問總的不會超過一分鐘吧,而是都是有經驗的記者,應一針見血,一分鐘的耐性真的十分寶貴。
回到家看有線新聞,卻見新的特首氣定神閒在回答記者問題前發表感謝辭,電視又剪輯了片段,聽收音機直播時那種不耐煩的感竟都清除了。
新的特首指自己是politician政治人物,不一定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表示已脫離公務員行列,不過他必須明白他的高民意與其公務員身份有深刻的關係,巿民期望曾蔭權以其管治經驗整頓香港。如今他明確為自己的工作以政治定位,向中央極力自我推銷,是必然的結果。
是日,香港繼續下雨。
RAINY NITE
在巴士上收聽十分鐘電台直播曾蔭權記者會,那是我聽個最湍急的記者會,但與回家後在電視上看見的,竟然有這麼一點點分別。
傍晚六時四十分扭開收音機,大概七、八個記者發問問題吧,不停環繞行政會議的組成、他會否在兩年任期後角逐新任特首等問題,只聽見新的特首不停打斷記者的發問,以強而有力斬釘截鐵的語調回答,「沒有」、「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對記者關注針對的問題,他了然於胸,但斷然拒絕友善溝通的感覺很強。記者每條發問總的不會超過一分鐘吧,而是都是有經驗的記者,應一針見血,一分鐘的耐性真的十分寶貴。
回到家看有線新聞,卻見新的特首氣定神閒在回答記者問題前發表感謝辭,電視又剪輯了片段,聽收音機直播時那種不耐煩的感竟都清除了。
新的特首指自己是politician政治人物,不一定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表示已脫離公務員行列,不過他必須明白他的高民意與其公務員身份有深刻的關係,巿民期望曾蔭權以其管治經驗整頓香港。如今他明確為自己的工作以政治定位,向中央極力自我推銷,是必然的結果。
是日,香港繼續下雨。
是日,曾蔭權遞表自動當選,下起黃色暴雨來。晚上等著出門與親友用餐,自然的驟變是無力挽。 這兩天好像多了評論批評李永達,沒有好好把握提名期做一個完備的政綱參戰,打從一開始便擺出必輸的姿態。可能是偏見吧,自從數月前壹週刊與剛接任民主黨主席的李永達的訪問後,便自然地將李永達打入「水份高」的窩囊族,也不見得他有特別的政見與政治魅力,只是不斷重覆一些慣見的政治詞彙。壹仔的人物專訪,在香港還真是頂呱呱。 今天電視新聞所見,李永達在落敗記者會上祝福曾蔭權,並期望曾氏能成功帶領香港。雖云似十足西方競選以君子的態度恭賀對手,但我更期望李永達能藉此機會最後一次狠批這次公關show的荒謬。近兩天曾蔭權落區的新聞已放到較後的位置,大家對這場表演的興緻真急速下滑。 原本,這是不必要寫的短文,曾蔭權當選也沒有什麼價值,但等停雨出門,大家多多包涵。
 WEN JIA BAO
WEN JIA BAO  講開版權,教書的常「借用」報章相片或裝飾來「美化」工作紙。現在的學生都好醒,印多兩頁參考書當然不是出版社教科書)或報紙都會問「你有無侵犯版權﹖」學校有向報紙買使用版權,好像印少過書的十分一及學校人數的某個百分比之內都可接納。你可以話我教書都唔尊重版權(正如我成日俾學生見到我朝頭早衝紅燈…),但基本上我好少顧忌,大佬,教書姐,quote晒source,非商業的教育用途,告我都無符。特別我們做校本課程,學生已鬼殺咁嘈話無書,張張notes飛下飛下,仲要成版字無圖﹖簡直趕客。
我又好忍唔到勁可愛白痴的公仔,除了用Microsoft的clipart外,最近教貧窮發現了RiniArt,圖像用作非商業及支持公民力量的活動應是免責的。近作是將溫家寶個頭用PhotoImpact加藝術效果放落工作紙,娛人自娛。
***
星期一的男人好唔得。放學時在地鐵先係俾個阿生用背囊撞,後在天后某阿伯望後唔望前,一轉身就成隻前手臂飛我個肚到,過兩個街口另一個阿伯既手肘撞落我手臂。
真係唔知究竟係人地失魂定係我「倫盡」。
講開版權,教書的常「借用」報章相片或裝飾來「美化」工作紙。現在的學生都好醒,印多兩頁參考書當然不是出版社教科書)或報紙都會問「你有無侵犯版權﹖」學校有向報紙買使用版權,好像印少過書的十分一及學校人數的某個百分比之內都可接納。你可以話我教書都唔尊重版權(正如我成日俾學生見到我朝頭早衝紅燈…),但基本上我好少顧忌,大佬,教書姐,quote晒source,非商業的教育用途,告我都無符。特別我們做校本課程,學生已鬼殺咁嘈話無書,張張notes飛下飛下,仲要成版字無圖﹖簡直趕客。
我又好忍唔到勁可愛白痴的公仔,除了用Microsoft的clipart外,最近教貧窮發現了RiniArt,圖像用作非商業及支持公民力量的活動應是免責的。近作是將溫家寶個頭用PhotoImpact加藝術效果放落工作紙,娛人自娛。
***
星期一的男人好唔得。放學時在地鐵先係俾個阿生用背囊撞,後在天后某阿伯望後唔望前,一轉身就成隻前手臂飛我個肚到,過兩個街口另一個阿伯既手肘撞落我手臂。
真係唔知究竟係人地失魂定係我「倫盡」。
 Sunday Dream.
Sunday Dream.  週末陽光好,去了游泳。只是半公共泳池,不要以為私人屋苑的泳池便很乾淨,人是一樣的多。未下水便想到同學表演的talk show話,在公共泳池游水﹖迫到只能在水池彈下彈下喳話!
在水底見到水面波光潾潾,甚是暢快,由此覺得在冷氣房做瑜伽實在無聊,在加洲的跑步機上跑呀跑的也太與人類自然本性相違。運動就是為了陽光嘛。
就是不明白,為什麼一家三口總要橫跨三條泳線教細路學游水呢﹖為什麼情侶總喜歡在泳池把對方抱起甜密的對望呢﹖為什麼這幾年愈來愈多女性喜歡著三點式到泳池呢﹖噢,我游水就真的是游水,一個人不停的游,偶爾揭起游水鏡曬面。還要穿全藍色一件頭泳衣,像極中學時參加泳賽的戰衣,十年不變。
***
本來想在網上找張泳池相貼上來的,但港燦那邊發生咁大件事,唯有貼張咖啡相。很久沒有打牛奶泡泡了,星期日手作仔,不要與機打的相提並論。
有時喜歡在明報新聞網下載相片,無他,自己是會員,下載正相容易。當然會藉沒有給我轉載片的權利。日後如何﹖唔知,再算。
週末陽光好,去了游泳。只是半公共泳池,不要以為私人屋苑的泳池便很乾淨,人是一樣的多。未下水便想到同學表演的talk show話,在公共泳池游水﹖迫到只能在水池彈下彈下喳話!
在水底見到水面波光潾潾,甚是暢快,由此覺得在冷氣房做瑜伽實在無聊,在加洲的跑步機上跑呀跑的也太與人類自然本性相違。運動就是為了陽光嘛。
就是不明白,為什麼一家三口總要橫跨三條泳線教細路學游水呢﹖為什麼情侶總喜歡在泳池把對方抱起甜密的對望呢﹖為什麼這幾年愈來愈多女性喜歡著三點式到泳池呢﹖噢,我游水就真的是游水,一個人不停的游,偶爾揭起游水鏡曬面。還要穿全藍色一件頭泳衣,像極中學時參加泳賽的戰衣,十年不變。
***
本來想在網上找張泳池相貼上來的,但港燦那邊發生咁大件事,唯有貼張咖啡相。很久沒有打牛奶泡泡了,星期日手作仔,不要與機打的相提並論。
有時喜歡在明報新聞網下載相片,無他,自己是會員,下載正相容易。當然會藉沒有給我轉載片的權利。日後如何﹖唔知,再算。
請了某政治人物來校演講。同事問我有什麼準則請政治人物來,「他們代表了某種聲音,學校要討論請人來有什麼準則…港英時代請錯人來演講,學校便會很麻煩。」現在會不會更麻煩﹖
我沒有什麼預設準則,只希望演講內容盡量配合課堂內容,讓學生看多一點便是了。(今天聽講完後,我更發現自己曾教錯東西!)當然我是不會請陳鑑林蔡素玉之流來的了,曾鈺成反而還可考慮。
學校是培養意識形態的基地。不能帶手機手繩漫畫電話都是一種世俗禮儀道德的預設標準。行為規範無傷大雅,意識形態便是大問題。對不起,如下面湯SIR說,我以一種道德批判另一種道德。不過這是現實也是我的想法,單一意識形態不是手段也不能是結果。無論中學大學都應提供空間讓學生尋求探索,而不是以多欺少為政治服務。
演講有預設立場是很正常的,就算是課堂教書都有立場罷。最近教貧富懸殊,說到中國民工受欺壓,不也是一種立場。工人是道德,難道老闆不是道德﹖道德標準是社會的一個最大公約數(這個term,都是最近看報紙才學回來的,都不知有沒有用錯,只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標準是會因時因地改變的。
尺度難以拿捏,正因如此,我們更不需要一個政治人物演講準則。
而我,也是不是太政治了﹖
***
明報這兩天走勢凌厲,繼昨日揭BT在媳婦考試前夕宴請考官後(只能說BT是笨),今天又偵查泳池女更衣室被人安裝偷拍器。那個頭版,啋,我在地鐵揭報紙,中一小男生便坐隔鄰,怱怱揭過,費事荼毒少年。回家,與細路李太齊齊分享。李太話,d麻甩佬,唉…
我,也是假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