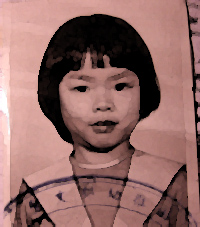好狗年
小時候,那有年初一下午便能安坐家中的可能。 那年頭,不是在街上拿著一袋二袋賀年夏威夷朱古力在撲的士挨家挨戶拜年,便是賴死在親戚家中看大人打麻將然後自己無無聊聊坐在沙發上等呀等,連娛樂版都刨埋,等到晚上七時八時傭人便走過來問你吃蘿蔔糕否。「唔食」,李小朋友通常黑著臉回答,當然也有說謝謝,不過無聊與無助感已打敗了禮儀與體面,所以以前我逢年初一都俾人鬧。 逢年初一最怕說恭喜發財龍馬精神一本萬利身體健康之類的話,所以初一早上起床便開始神經緊繃,迫著開始一天的恭賀新禧話劇表演,利是錢也利誘不到我以平靜和諧的心情說兩聲意頭話。李老闆逢初一都要打電話到外國向親戚拜年,在李小朋友還沒有心理準備下突然傳電話過來︰「你等等呀吓,呀女話要同你講兩句…」唯有乾笑兩聲,用非常生硬的語調同姨媽姑姐拜年。 今時唔同往日啦,早幾年傳統已經衰落。莫講話長者們,見上帝者見上帝,移民的移民,李老闆今時今日都唔打電話,改用SMS拜年︰「呀女,字母要轉做大楷,點轉﹖」到我還是戰戰兢兢問李太,初幾先可以去街,李老闆竟然初一晚就去打麻雀!咩傳統都無晒,李老闆,攪到我媽媽聲,當然只可在心裡咆哮,否則仍會被「開年」。 飲完茶搭車返歸,我問李太︰「你點過渡三十歲的危機﹖」答曰︰「三十歲果陣,我咩都有啦,結左婚,你都幾歲咯,危咩機…」可憐我快三十,快者,不過今年過埋生日都未三十呀吓,仲係裙腳妹囉。由此悟到,未有自己的家庭,更不用說生了兩件要抱來抱去拜年逗利是,新年氣氛就梗淡薄點。所謂節日氣氛,事在人為囉,今晚我同李太同細佬響屋企食白切雞,呵呵。